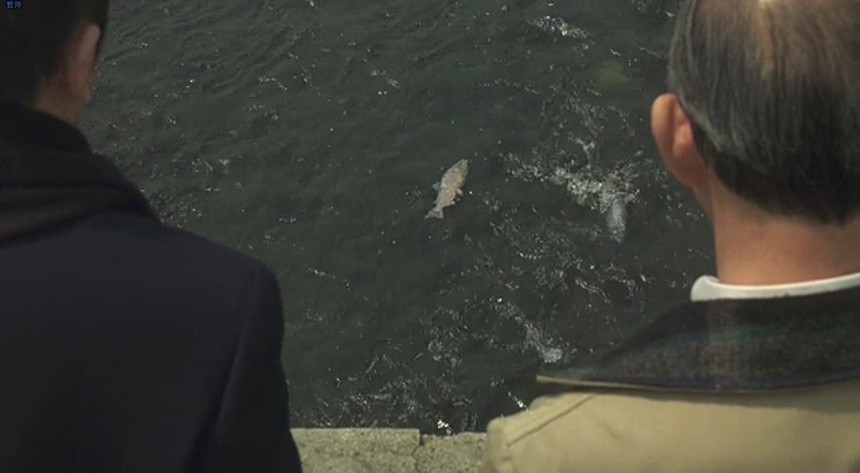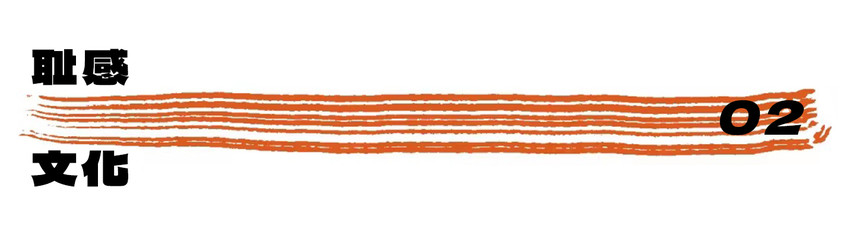影片《入殓师》根据日本作家青木新门的小说《门纳棺夫日记》改编而成,由泷田洋二郎执导,本木雅弘、山崎努、广末凉子、吉行和子和笹野高史等联袂出演,获得第32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高大奖、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等奖项。影片以小林大悟这一新手入殓师的视角,走入他的生活去窥窃死亡,凭借入殓礼仪展示日本社会语境下个人情感在“耻文化”和“罪文化”的传递。

/
现代的日本的大和文明是以父权制度同家为中心的集体主义组建而成。日本社会是一个男性气质显著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往往表现出男女社会地位不同。日本男性很少或几乎不参与任何家庭劳动, 这不仅是因为大多数女性结婚后选择做家庭主妇, 还与日本社会的性别歧视现象有关。在日本社会即使是工作的女性, 他们的工资也仅占男性工资的六成左右,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女性的参与度更低。因此, 在男性气质显著的日本,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男性则更多的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影片虽然不是典型的日本家庭,但是大悟夫妻二人的关系也是日本家庭的一个缩影,表现出了日本父权社会下的典型的男性气质与隐忍的日本主妇形象。
影片中,大悟的妻子美香虽然有自己的工作,但影片全程却没有过多描写,在丈夫失业下柔顺地跟随丈夫前往乡下,没有指责与抱怨,甚至在小林大悟在第一次接触死亡两周的尸体后,大悟依靠妻子的身体以性爱的冲击摆脱当前事物带来的恶心与压力,从美香的自我牺牲与性情的温柔、对家庭支持、隐忍、顺从中可见日本父权社会的地位。
其次,在缺失父亲角色的家庭成长的大悟,电影中的 “社长”这个角色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父亲的位置。
在大悟失业的时候给了他工作,同时也成为他工作上的导师,在大悟第一次面对尸体的时候给予了严厉的指导,而且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着严厉与认真,电影中能感受到主人公无限服从的家庭观念,使得大悟甘愿并接受了入殓师这样一份工作,也暗喻着日本父权社会下的 “子承父业”理念。
日本是一个十分注重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日本国民从小就接受集团意识的教育,对集体的依赖也使日本国民产生了强烈的服从意识,要求集团中的个人要为了集体的协调,要讲“和”,要学会克制和容忍,追求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日本国民为了维护集团间稳定和谐的秩序,常常会掩饰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不能真实的表达自己,集团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日本国民个性的发展。如当接到乐团解散的通知时,大家没有任何反应,只是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大悟虽然感到了吃惊, 却压抑自己内心的伤心与愤怒。
传统的日本电影和日本社会相对来说是保守的,更加喜欢被社会同化和妥协,这就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父权意识、家庭意识和集体意识。但是这部电影所传达的家庭观念其实是被削弱甚至是剥夺的,电影中的主人公是独立存在的一个个体,他所追求的也是个人情感上的传递和满足,而影片本质上仍然是向日本传统的 “家” 文化靠拢的,在独立个体与集体主义的矛盾下所带来 “耻文化”和负罪感使人物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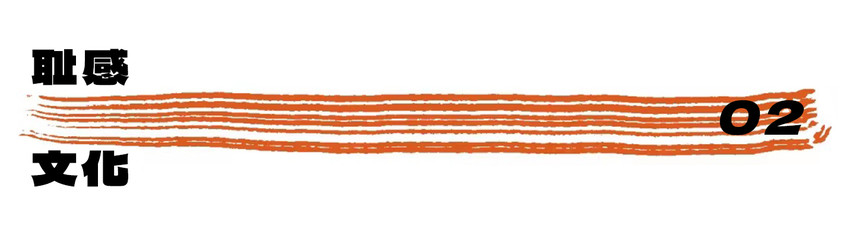
日本国民的耻感文化与集团意识是密不可分的,一个人的集体归属感越低,它的羞耻感就会越强烈。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评价,日本文化的一个特点——耻感文化。而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对大量资料分析后,给日本文化下的定义,是在区别于西方 “罪感文化” 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耻感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耻感这种心理感受加以发掘、升华,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积淀,对国人的行为和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志着一个国家性的文化。
从这部电影中大悟的社会活动范围以及特点来看,小林这个人物的羞耻感的来源更多的是对于集体归属感的迷茫,这是日本社会的基本特点,所以我们大致也可以推断小林的罪恶感从何而来。
当大悟获得入殓师工作时就面临着与社会认同的矛盾,他之所以感受羞耻是因为这份特殊的工作没有 “集体归属感”,不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与其说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不如说是大悟这个角色内心世界的矛盾。大悟的这种羞耻感让他不得不去承受来自家庭以及社会的指责和压力。

“罪感文化”的核心是劝人向善的,是在西方基督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自我救赎的文化,一个人的错误都是来源于自己内心世界的,在大悟犹豫后坚守着入殓师的工作实现了自我价值,得到救赎,对于自己职业以及对于自我的认识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不受到外界的影响。
“真是罪过呀。”,社长一边吃着烤河豚一边感叹着,一个物种的生存是以另一个物种的生命为基础,开解了大悟让大悟脱离了入殓师的耻辱感的外部影响,懂得工作是为了生存,所谓的烦恼是他人给的,就此放开。
镜头下,以大悟、社长和经理小姐,每个人的单一镜头拿起鸡腿、鸡翅去享受,多个特写含有鸡腿、鸡翅的骨头与卫生纸至后面人物的同框镜头可见,人物在罪感下成长注重内心世界的愉悦,有自然存在的价值,是自我价值和认同上的追求并脱离了 “耻” 的外部影响,追求着内心世界的救赎。与其说大悟的妻子同友人、世人所接受入殓师工作,不如说他们接受了礼仪制带来的参与感,服从了集体制度下工匠精神与个人耻感的矛盾而带来的罪感文化。
入殓礼中,日本人冷静地对待死亡,保持的是一种平静式的忧伤,可以说是物哀文化的一种,追求着至美的情怀,大悟在仪式下把失去的人重新唤回,赋予永恒的美丽,为其擦拭、化妆,让家人对往生者告别,在平缓下人们的深情凝聚在一起形容一种集体,彼此在身体和灵魂上得到洗礼,获得罪感中的救赎。
本文通过影片《入殓师》这扇通往生死的大门,打开从职业观与家庭化的日本文化特点产生矛盾的耻感和罪感,带领人们彼此得到救赎。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人民他们强烈的集团意识和源于内心深处的耻感文化,在对待工作仪式的敬畏与尊崇之心,使得每个人内心的罪感得以成长,彼此在平静中前往“往生”。
参考文献:
[1]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新世界出版社, 2012.;
[2]土居健郎.日本人的心理结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3]王立波.日本家庭主妇阶层的形成[J].社会, 2004 (11) .;
[4]张艳萍,王欢.关于日本电影《入殓师》的社会学思考[J].唐都学刊,2012(01).;
[5]曾晓霞.从电影《入殓师》剖析日本社会的矛盾本质[J].电影文学,2013(07).;
[6]王丽宁,从电影《入殓师》浅析跨文化交际现象
[7]杜彬彬,电影《入殓师》东西方文化的博弈与冲撞